|
(續上頁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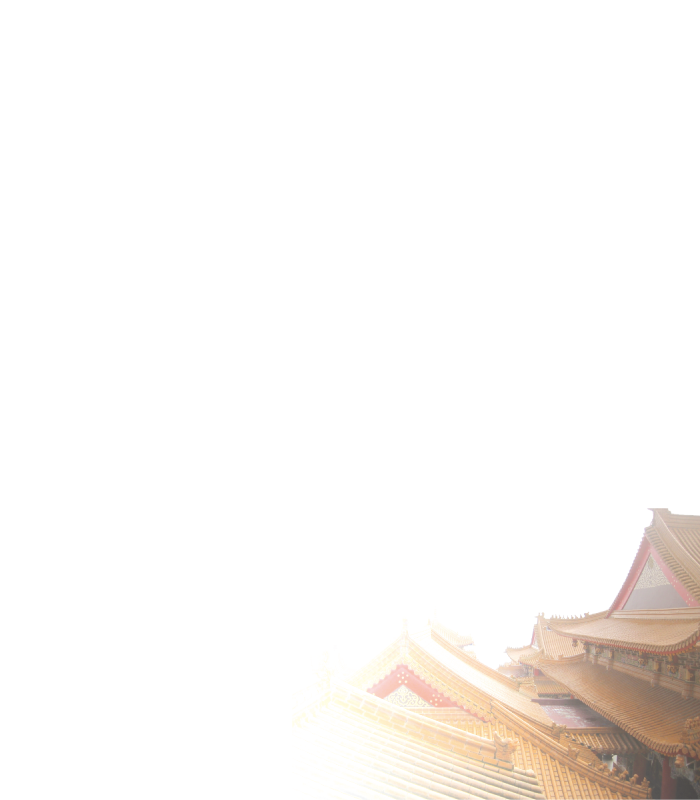 對於回歸個人這種態度,高行健以「冷」文學稱之,依我個人的淺見,這種態度缺少積極的成分,並把作者限定為觀察者的角度。高、劉兩位學者所提「走出二十世紀」、「回歸文學的自性」的呼籲,忽略了定義文學的責任,其所謂「回歸文學的自性」之「自性」,指的僅是個人的本性而已;簡單的說,「回歸文學的自性」指的乃是文學的「出家」,可反轉胡適先生的社會觀點來加以詮釋:作者該自「大我」回轉到「小我」,而此結論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趨勢正好相反。劉再復進一步從高行健個人的例子歸納出一個共同的現代文學理論,此即為「中國現代文學可以分為兩大類型:一個是熱文學類型,一個是冷文學類型」。此結論頗可懷疑,依我看來,「冷」文學或起源於「熱」文學之壓迫,或為文學有意無意地與時代切斷聯繫。高、劉兩位學者在此會談中,僅談及他們所認為的寫作態度方面的一種趨勢,我卻認為為了觸及問題的癥結,非從文學之傳統著手分析現代文學不可。 對於回歸個人這種態度,高行健以「冷」文學稱之,依我個人的淺見,這種態度缺少積極的成分,並把作者限定為觀察者的角度。高、劉兩位學者所提「走出二十世紀」、「回歸文學的自性」的呼籲,忽略了定義文學的責任,其所謂「回歸文學的自性」之「自性」,指的僅是個人的本性而已;簡單的說,「回歸文學的自性」指的乃是文學的「出家」,可反轉胡適先生的社會觀點來加以詮釋:作者該自「大我」回轉到「小我」,而此結論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趨勢正好相反。劉再復進一步從高行健個人的例子歸納出一個共同的現代文學理論,此即為「中國現代文學可以分為兩大類型:一個是熱文學類型,一個是冷文學類型」。此結論頗可懷疑,依我看來,「冷」文學或起源於「熱」文學之壓迫,或為文學有意無意地與時代切斷聯繫。高、劉兩位學者在此會談中,僅談及他們所認為的寫作態度方面的一種趨勢,我卻認為為了觸及問題的癥結,非從文學之傳統著手分析現代文學不可。
從二十一世紀的角度來說,中國文學有兩個傳統,二十世紀之前的上古、中古以至於近代的文學發展是為大傳統,五四時期的文學則為小傳統。白先勇恰好接受了這兩個傳統的薰陶,因此我們可以預料他給當代文學所下的定義,與上述高行健的主張不會發生共鳴。雖然白先生之創作亦以「人」為主,但其「人」的概念卻不限於個人的本性,而是包含「人類的情感」。就其見解而言,寫「人類的情感」之著作,才能以文學自居,倒是「個人的感情,寫一寫,很快就寫完了」。該主張顯露出一種關心社會的態度,也是一種容易被誤解的態度;其實白先生未嘗忽略個人,他以重視個人與社會、眾生及歷史的相關性,進而從個人的體會和情感寫出眾生的體會和情感。如此的寫作方法必須從推己及人著手,因此而產生的作品即可代表人生與時代,足以讓讀者心有同感焉。至於「抓住自己的文化」,當然是寫作的必備條件之一,這一點對白先勇而言也十分迫切。中共在文革時期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遺產,因而身為首位中國當代作者,把「挽救自己的文化」當作重大使命;說得廣泛一點兒,因為在中國近代史發生了文革這個大悲劇,所以當代作者必須負起把「已經被推倒的中國大傳統銜接回來」的重大責任。這乃是白先勇補償文革所留下的傷痕的作法。高行健卻不然,他把作者變為「隱士」,視之為對付文革所創造之空洞的最佳方法。
讓我們最後看顧彬教授如何評論中國文學的現狀。顧彬教授曾頗激烈地批評中國當代文學之狀態,他對此所提出四點不滿:首先他認為中國作者往往不能充分把握中華語言,其次他們缺少勇氣;再其次當代中國作者不夠認真,往往把寫作當作副業而已;最後的不滿則與高行健類似,即是文學逐漸市場化的現象。顧彬所建議的出路卻與高先生不同,「回歸傳統」是顧彬教授的重要主張,此主張很接近白先勇的立場。
傳統的古典文學究竟意味著什麼?它包括思索正確的生活方式為何、如何應付劫數、何謂死亡、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在時局中存活等課題,無論從哪一方面深究,古代文人皆尊重「道德乃是勇氣」這種精神。
因此之故,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,與其說是從「熱」文學變成「冷」文學,不如說當代作者沒有把握中國傳統所留下來的文學遺產,因此不知從何著手,或者是乾脆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。劉再復所謂「熱文學可以魯迅為代表」之言,倒可說魯迅還充分地把握了中國文學的大傳統,而當代作者往往及不上這一點。「冷型」的高行健把握了傳統與否,我就不敢說了;但如果像他所述而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界有一種從「熱」到「冷」的趨勢,這話恐怕說得太不具體。
|